【编者按】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李晨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应新雅书院邀请,将于2023年春季学期4-6月担任“新雅书院驻院学者”,为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国际哲学前沿》课程(14700323-0,后八周课,本研均可选)。课程助教周心仪(哲学系硕士生)和郝悠扬(新雅书院2019级PPE)、梁奕飞(新雅书院2020级PPE)等同学在开课前在线采访李晨阳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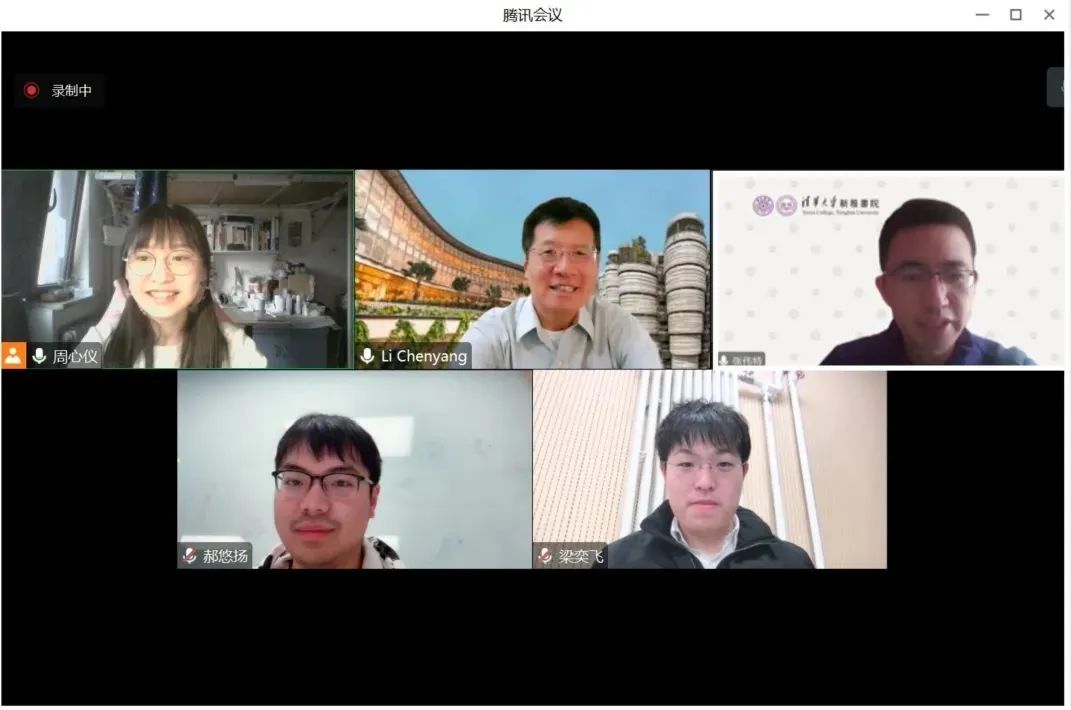
采访合影
学者简介
李晨阳(Prof.Chenyang Li):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创系主任,著名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前任会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分别获得哲学学士(1982)与哲学硕士(1984),1992年获得康乃狄格大学博士。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美国曼莫斯学院、中央华盛顿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系主任。自2010年起,应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负责创建哲学系。研究兴趣主要在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已发表百余篇论文及多本哲学专著,任十余家学术刊物编委。著作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杜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用作教材。在当代国际比较哲学、中国哲学领域是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之一。
名师访谈
01.学教漫谈 访谈人:郝悠扬
Q:我们希望能够跟老师聊聊您的学习经历和从教经历,我想这也是我们刚刚进入哲学学习的同学最受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您是在恢复高考之后就报考了哲学专业,在当时可能哲学学习的氛围和学术基础都还不是很成熟,您自己在当时是怎么样投身于哲学的学习呢?
A:我当初报考哲学系的时候心目中想象的哲学和现在理解的哲学非常不一样。我高考之前在山东的一个地方政府做秘书,那时非常羡慕有理论的人,我觉得能写出大块文章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高考的时候就考虑尽量学一些理论知识装备自己,以便毕业以后还能做类似的工作。另外一个认真考虑过的学科是数学,当地一位专科学校的老师建议我去学数学。但是我对做数理化的工作了解的比较少,不太清楚什么叫科学研究,后来又觉得每天做数学研究也挺枯燥的,最后还是选了哲学。那时对哲学的印象和理解与现在很不一样,回头看我也不后悔,直到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前我都是想着回去做实际工作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哲学系让我留校,想想当老师也不错,后来出国读了博士,其实是一步一步过来的,并不是开始有很明确的目标,现在就到这里了,这就是我怎么进了哲学系,开始做哲学的过程。

李晨阳教授在线接受访谈
Q:您是怎么样把中国哲学的研究逐渐拓展到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呢?在您学习的年代可能中国哲学还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下开展的,还想请老师谈谈您的研究从中国哲学拓展到比较哲学的经历。
A:我们读本科的时候,北大哲学系特别重视哲学史知识,两门比较重要的课就是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每一门课要修两个学期,是很系统的训练,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积累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到美国读书,博士主攻方向是西方哲学,但我的导师乔·考普曼(Joel J. Kupperman)是当时美国哲学界少有的做比较哲学的学者,他中西印都做一点,我受他影响比较大,但自己的论文研究还是以西方哲学为主,添加了一些中国哲学的视角,算是有点儿比较哲学。
毕业工作以后,兴趣逐渐偏向中西比较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研究。我的第一份教职是在一个私立的文理学院,它的课程设置特别强调打通各种专科,这也间接地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发展。后来我做的比较哲学的研究受到一些关注,博士论文中有比较视角的一章获得美国哲学学会的最佳论文奖,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部分其实是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的两章。我想,做研究也有点儿像市场一样,学界的关注也鼓励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做,比较哲学的视角切合我的研究方法,切入了西方哲学的角度,而且引入了中国哲学的一些问题,英文读者群容易关注,后来基本上就按照比较哲学的路数走下来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规划,做学问写了东西有人读是很高兴,很受鼓励的事情。自己又感兴趣,就一路过来了。
Q:您认为,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中如何建立不同哲学体系对话的方式?我们比较的基础是什么?比如说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差别是在方法上,西方哲学强调逻辑论证,中国哲学更偏重直接说理和生活体验,还有人认为是偏重领域的不同,西方哲学更关注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中国哲学更关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想请教老师我们在谈“比较”的时候是在什么平台上使比较和对话成为可能的?
A: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认识比较哲学的问题,比较哲学不是仅仅比较不同哲学的长短高低。一般认为比较哲学分两个层次,例如波士顿大学的Robert Neville比较早表述的,一个是客观的研究过程(the objectivist approach),就是了解不同传统的哲学著作,通过比较来了解他们是什么观点,看看孟子是怎么说的,看看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比较之后加深对他们各自的理解,这是一个客观的角度,不比较往往是不知道的。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经常送学生去中国、印度、欧洲去交流,他们回来之后跟我说有两点感触,第一,去其它国家/地区了解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第二,以此做对照,更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去之前不知道某个东西是美国人独特的东西,去了之后才知道这是美国特点。这就是比较方法的长处。通过比较要研究的文本的特点,这是比较哲学的一个方面。
在当代做中国哲学其实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Neville叫规范性的研究(the normative approach),这是比较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根据你了解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要怎么样解决哲学问题,提出哲学观点。这是建树性的工作,仅仅在自己的传统中也可以建树,但在比较哲学中你的视角更广泛,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个工作也是属于跨文化研究,这是比较哲学在当代更重要的工作。现在国内很多做中国哲学的学者对西方哲学了解也比较深,不少西方哲学的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也比较深,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环境的改变。如果仅仅作片面的理解,认为比较哲学只是比较长短高低,比较哲学在当代的意义就很有限,这次讲课我和黄勇老师都希望与同学们一起探讨,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哲学问题,这个特点我们都是一以贯之的。
Q:这些年国内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者都在逐渐试图通过中西汇通来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比如阳明心学和现象学,斯宾诺莎和理学中的气论,因为李老师也是在中国和西方学界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希望您能够谈谈两边学界在比较哲学研究上的差异。
A:我觉得国内比较哲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研究,做构建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最近有一些,尤其是一些五十岁左右的学者开始努力而且做的比较好,我希望到了你们能够进入学界的时候能做的更好。
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大体包括两种学者,一种是有中国思想史背景,他们可能对西方哲学了解并不多,虽然是在西方学界。把自己做成中国思想史的专家也不容易,要学中文,了解中国历史和哲学。另一种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而不是研究哲学史的,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内容的时候,眼界逐渐开阔,加入了一些中国哲学的材料到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去。第二部分人,数量不好统计,但可能比第一种人的数量更大一些,他们往往是从哲学问题的角度来研究的,主要是构建性的。某个问题在西方是这样表述的,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从哲学本身的问题来寻找一些中国哲学的资源,也是蛮有意思的一种进路。
Q:您对大一大二刚刚进入哲学学习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和提醒吗?
A:我想提三点建议。首先,你一定要喜欢这个学科,如果不喜欢就不要急着做,你喜欢就觉得它非常有意思,你发展不出兴趣来就会觉得很枯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发展出这种兴趣,所以这个很重要。也可能原来觉得有意思,后来发现兴趣转移了,这个也要慎重考虑是不是要急着做。问问自己究竟是不是喜欢,不要自欺。
第二点,多想一想怎么去做,做哲学大体上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做思想史和历史研究,这是一门非常坚实的学科;另一条是以问题为主,提出哲学的问题,做出哲学的东西。这是很有挑战性也很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做哪种基本功都很重要。
第三点,无论做哪一种,在大学期间要好好读几本经典著作,不用很多,能熟悉五、六本就不错,可以参考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为坐标给自己定位,来开辟你的进路,。另外对当代的哲学家要有一些兴趣,也要参考当代的一些观点。
02.前沿对话 访谈人:梁奕飞
Q:关于比较哲学的方法,您认为对于根植于不同语言与文明传统的哲学体系,应该用“比喻”而不是“对应”的方法进行比较。以您在《道与西方的相遇》中举过的例子比喻,我们不应该追求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而是应该在保留三角形基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方法如何确保它的精确性?如何确保最后做出的仍然是三角形而不是其他形状?
A:这是很好的问题。首先精确的比较,尤其是在差异比较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确比较是困难的。哲学是对我们生活的经验世界的概念化,在哲学的抽象的层次上,不同文明的概念化方法取向和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找到严格的对应关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大问题,是不是给比较哲学造成很大困难?我觉得不会。
美国学者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主张,概念就是比喻性的,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如此。我们是通过比喻来思考的。概念不是柏拉图或者康德所说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生活中慢慢积累、在一个文化中通过不同人的合力形成的。因此概念必然是交叠的(overlapping),在同一个文化中的同一个概念每个人的理解也不是完全全等的。比如,英语中giant的意思是巨大的,但是它最早是一个名词,指的是一种大的东西,后来不同人的理解不一致,才转变成大的概念。中国古文中也有相似的现象,同一个词的意思边缘是不确定的。
跨文化的研究中的确会遇到跨度比较大的情况。比如儒家的“仁”的概念在西方就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来表述。因为“仁”最早的含义是比较具体的“仁爱”,有善良、温存的意思。后来在孔子那里又发展成非常全面的“成仁”的德性。这两个意思之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文中的一个字在英文翻译中就得用不同的意思来解释,“仁”可以是humanism、kindness、universal virtue或者humanity,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解释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么解读大家觉得可以接受,不是完全的主观臆造,这是用外文研究中国哲学常有的问题。
再比如西方的“自由”的概念,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康德、萨特,每个人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具体定义的自由,我觉得不应该是问题。因为柏拉图也没有康德的自由,奥古斯丁也没有康德的自由,对吧?但是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没有自由的概念,我觉得说不过去。中国哲学中有自己的表述自由的方式,比如《荀子》、《孟子》中对自由的论述找不到西方学者那样单独篇章的《论自由》,但是我们对它们论述重构(reconstruction)之后还是能看到关于自由的论述。因此我们就要从中国哲学本身来考察,可以参考西方不同的自由定义,来解说或者重构中国哲学中自由的概念。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只要不把比较看作寻找一对一完全对应的研究,比较是完全可能的。哲学研究不是植物史研究,也没有DNA检测这种手段,哲学中一对一完全对应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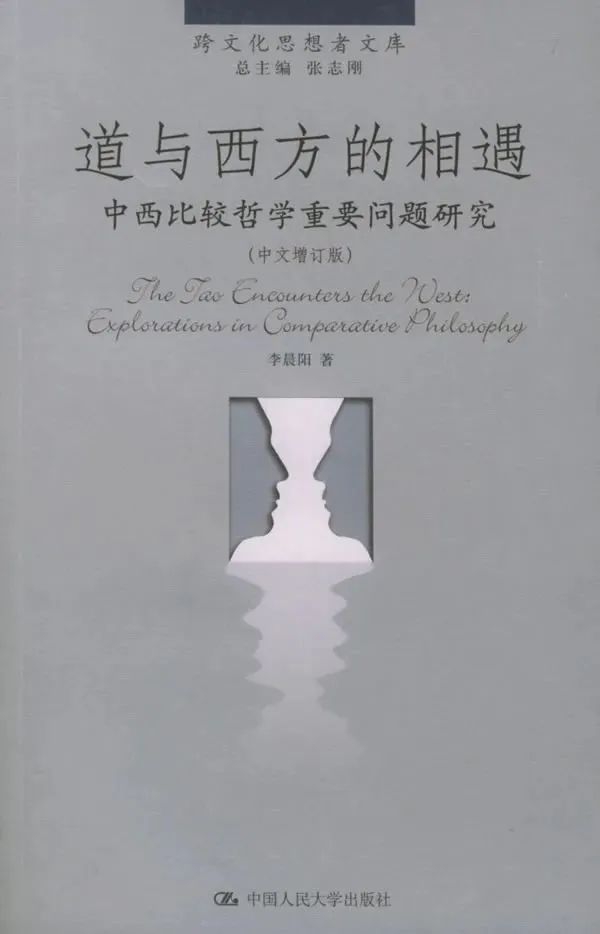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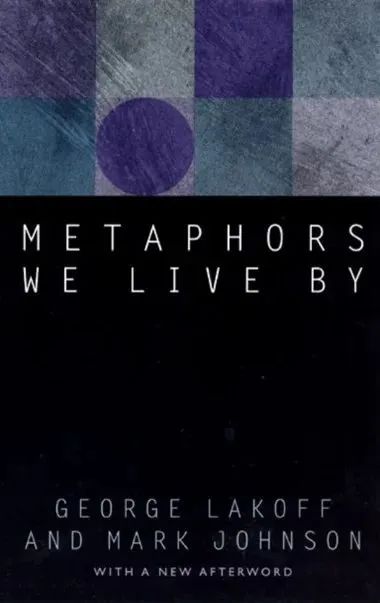
书影
Q:您认为和西方比较来看,中国的宗教是多元参与的。我理解这种多元性不仅仅是同时空的共存,更是在同一个人精神上的共存。如果按照韦伯的观点来看,这是宗教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形态。您总体上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A:首先从概念层次来讲,从多神教到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一个升华过程。从具体的山神、水神到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要求有更高的抽象思维能力。黑格尔认为从早期具体的多神崇拜到一神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从概念上来看是有这个过程的。
但是从宗教的实践来说,我不同意崇拜一神教比崇拜多神教更进步。无论哪一种宗教都可能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也可能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糟。你对我的观点的理解是准确的,我基本上是以儒道互补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宗教。我的祖父祖母那一代还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但是他们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儒教,而是什么都信一点。以西方为主的一神教在一个人身上没有这种多元特色,但是在实践上来看,抽象的一神在不同人的理解和想象中也是不一样的,甚至也会不断变化,这也类似于多元宗教的实践。当代西方基督教哲学家John Hick对现代基督教的解读认为每个人对同一个神圣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就像康德的物自体一样,它不是具体的事物,但是没有它又不能解释现象世界。不同宗教对这个物自体表述不一样,但是就像从不同角度看同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是对同一个物自体的不同表述。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对同一个宗教不同人的理解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同一人也不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固定的理解,这就有点类似于不同宗教的实践形态。
Q:您如何理解中国哲学进入现代社会的问题?中国哲学和汉语哲学有何区别?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您觉得有哪些方向我们应该重点关注?
A:现代性以及前现代、后现代的概念大家定义的差别很大,我一般不太用这些概念。现代性的概念我的理解是代表欧洲在中世纪后越来越依赖基于同一性的理性的趋势。比如,康德认为每个人按照理性思维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因此不可能出现道德的两难情况。理性对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社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说后现代意味着我们要抛弃理性,我不赞成。做哲学没有理性不行。
汉语哲学我了解不是很多,我的大学同学韩水法教授在北大有一个汉语哲学中心,也办过学术会议,但是时间冲突原因我没能参加。我理解汉语哲学是用汉语做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哲学研究对语言的依赖比较大。有人说德文是唯一的哲学语言,虽然有点夸大,但是德文确实哲学专业性比较强。用中文做哲学也会有些自己的特点,这些需要研究。我还了解不够多,但是我希望这种研究不要过于强调我们的民族性,而降低了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更不要强调中国哲学只有在汉语哲学中才能做出来,这样就相当于作茧自缚了,如果有这种倾向,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所以我认为汉语哲学的研究,是为了研究汉语做哲学——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独到之处,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不希望这变成一个范围,只有在汉语哲学里面才是真正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等等,我们应该有这种警觉。
Q:您认为从比较哲学的视角来看有没有评价不同哲学体系优劣的、超越比较哲学框架的标准?
A:我不认为会有超越具体文化之上的统一的、普遍的标准,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认为评价一个哲学体系也不需要一个超越具体体系之上的独特标准。哲学发展肯定有相对先进相对落后的衡量判断,比如我们不可能认为第一个中国人就达到了孔子的高度,在一个传统或者体系之内肯定是有哲学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一个传统内部是可以评价的。
同样如果站在另外一个文化传统中,是可以认可这种评价的,可以说孔子比他以前的人进了一大步,也可以说黄宗羲引入现代社会的一些概念,又比孔子、孟子进了一大步。或者也可以不同意,认为黄宗羲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贡献,这都是可以的。因此也是可以评价的。
这样就不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普遍标准、超文化标准,但还可以对文化的进步、哲学的发展作出评价。所以比较哲学研究没必要找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我们不能拿西方的标准作为一种普遍标准,因为西方本身也是一个被评价的体系,要用自己的评价体系抬高自己,就不合适。比较哲学之中肯定会有聚焦点的差异,你从西方哲学考虑,我从中国哲学考虑,我们有些地方可能同意,有些地方可能不同意,这都是可以评价的。这个问题很好,值得进一步研究。
03.课程导览 访谈人:周心仪
Q:您的《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一书曾归纳过近代以来儒家传统面临的五个挑战,即来自科学、民主、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的挑战和儒家传统自身生存的挑战。这学期您在新雅开设的《国际哲学前沿》课程选取了第三个挑战,即儒学与女性主义哲学的相容问题作为重要的话题,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高或解决的迫切性更高吗?
A:首先这门课不是想全面地回应儒家所遇到的问题,我的重点是跟同学们展示一下当前做儒家哲学,尤其是从比较哲学角度做儒家哲学的一些做法。国内的朋友往往是用传统的历史的做法,而年轻的朋友对现有的一些做法可能了解不多,我想通过这个机会,跟黄勇老师一起向大家展示一下当前做中国哲学的一些可能是新的、比较引人注意的方法。至于儒家遇到了什么问题、儒家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是本门课程的重心。
我们有一周的课跟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有关。那么为什么选择女性主义的问题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主流的学者似乎对这方面的敏感程度不够、了解程度不够、重视程度不够。其实女性主义哲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它牵涉到当代我们怎么理解道德哲学的本质、怎么理解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怎么理解情感和理性这两方面在一个取得相对平衡的生活中的关系。从这几方面来说,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李泽厚讲的中国的情理结构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时候必须情理并重,而从西方关怀伦理学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借鉴,这就是这门课选择“Confucian Ren and Feminist Care”这个话题的一些考虑。不过,这门课主要还是想让同学们了解一下我们做中国哲学的做法,给同学们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至于同学们能不能接受,那由同学们自己决定。
另外,我今年要出一本书,Reshaping Confucianism。第一周的课我会跟同学们分享其中的导论部分,主要讨论方法论和如何构建当代的儒学。可以让有兴趣的同学先睹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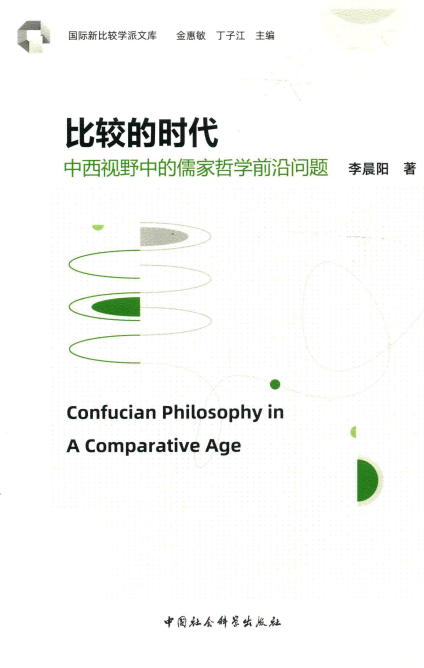
书影
Q: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除了帮助同学们了解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方法之外,您还期望同学们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A:首先希望大家了解这种做法,对我和黄勇老师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印象。我不是说我们的做法是很独特的,现在国内有些学者也开始这么做,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研究方法还是属于少数,尤其在英文语境中。我们的做法可能比国内的中文文章在方法层面更突出一点,更容易被你们察觉。
其次,也希望给同学们展示一下目前重要的哲学问题有些什么样的讨论、有些什么样的可能解决办法,让大家对这个领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Q:学习这门课程需要什么样的背景知识?选课的同学应该怎么样做一些课前准备?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A:我个人觉得哲学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技术性要求很高的,必须经受过很严格的学术训练,对这个领域的专业词汇非常了解;第二种不需要很过硬的专业训练,主要是通过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门课主要偏向于第二种。就这门课而言,只要能读懂英文、并且对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事实有所了解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希望做一些课前准备,可以提前读一读我们的阅读材料,在上课的时候带着阅读时发现的问题过来,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如果有更深的兴趣,还可以把阅读材料中提到的参考文献读一读,反思文章的文本解读和基本论点是否正确。其实很多新观点都是从课堂上的不同意见发展出来的,希望同学们在阅读时能多下功夫,在这门课上有所收获。
课程信息
课程:国际哲学前沿:比较哲学角度下的儒家哲学
序号:14700323-0
教师:李晨阳老师(9-12周);黄勇老师(13-16周)
时间:星期一(9-16周)09:50-12:15;星期五(9-16周)13:30-16:05
地点:四教4303
考核:2篇论文(5000-8000字)60%;4次读书札记(1000字)40%。
联系:张伟特老师(weitezhang@tsinghua.edu.cn)
助教:周心仪(1147966849@qq.com)

课程群二维码
欢迎对本门课程感兴趣的同学扫码进群!
课程大纲
Week 9: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World Philosophy: Methodological Issues
(1)Reading: Li Chenyang,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World Philosophy,”Asian Studies2022 (10.3): 39-58;
(2)Reading: Li Chenyang, “Introduction to Reshaping Confucianism”.
Week 10: Ren and Li in the Analects
(1)Reading: Kwong-loi Shun, “Jen and Li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and West 43 (3):457-479 (1993);
(2)Reading: Li Chenyang, “Li as Cultural Grammar: the Relation between Li and Ren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 West, 2007, Vol 57.3: 311-329.
Week 11: Confucian Ren and Feminist Care
(1)Reading: Li Chenyang, “The Confucian Ren and Care Debate: Re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Philosophy Compass.2022; e12868. https://doi.org/10.1111/phc3.12868;
(2)Reading: Li Chenyang,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en and the Feminist Ethics of Care: A Comparative Study”,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1994, Vol 9.1: 70-89.
Week 12: The Eight Human Aims in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Good Life
(1)Reading: Li Chenyang, “The Sequential Problem of Human Aims in the Great Learning”, Philosophy East & West. 73:2 (April 2023).
(2)Reading: Li Chenyang, “Material Wellbeing and Cultivation of Characterin Confucianism”, in Moral Cultivation and Confucian Character: Engaging Joel J. Kupperman, eds. Chenyang Li & Peimin Ni. Albany, 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171-188.
Week 13
(1) Why Be Moral?
Reading: Chapter 1 of Yong Huang, Why Be Moral: Learning from New Confucian Brothers, Albany, 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4.
(2) How Weakness of the Will Is Not Possible.
Reading: Chapter 3 of Yong Huang, Why Be Moral: Learning from New Confucian Brothers, Albany, 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4.
Week 14
(1) Is Virtue Ethics Self-Centered?
Reading: Yong Huang, “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4 (2010).4: 651-692.
(2) How Is Virtue Ethics Possible?
Reading: Yong Huang, “Two Dilemmas of Virtue Ethics and How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voids Them.”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36(2011): 247-281.
Week 15
(1) Moral Realism
Reading: Yong Huang, “Agent-focused Moral Realism: Zhu Xi’s Virtue Ethics Approach.” (To be distributed)
(2) Knowing-To: A Neglected Type of Knowing
Reading: Yong Huang, “Knowing-that, Knowing-how, or Knowing-to: Wang Yangming’s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42 (2017): 65-94.
Week 16
(1) Empathy with Evil
Reading: “Empathy with ‘Devils’: Wang Yangming’s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Moral Philosophy,” in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Michael Mi, Michael Slote, and Ernest Sosa (Routledge, 2015), 214-234.
(2) Moral Luck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Reading: “Moral Luck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Wang Yangming on the Confucian Problem of Evil,” in Wh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Still Matters. Ed. Mingdong Gu(Routledge, 2018), 6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