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雅一向重视学生的阅读与写作,强调在大量阅读与小班研讨基础上的思考与写作训练。近年来,学生的一些课程习作也在“卿云杯”通识课程论文大赛、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政经哲杯”书评大赛等活动中取得一些成绩。接下来我们会陆续刊出其中的几篇优秀作品。本篇为新雅书院2017级高靖涵同学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课上的一篇习作,该文获第一届“卿云杯”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三等奖。
虚无、流亡与联结
——《死者》中的三段冲突
新雅书院2017级高靖涵

《死者》作为小说集《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可以说是全书的高潮与总结,更是一部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思想史。笔者认为,《死者》中宴前、宴中、宴后加布里埃尔与三个女人发生的三段冲突,同时也是三次与历史发生联系的尝试,并将由此来解读乔伊斯对时间、民族和生死等问题的思考。
一. 莉莉、爱佛丝、格丽塔
加布里埃尔一出场,就与看门人的女儿莉莉发生了一段“冲突”。“还是个孩子时加布里埃尔就认识了的”[1]莉莉,此时在他眼前却是如此的陌生,以致于和她的对话处处尴尬。这是他第一次回忆,第一次试图与历史产生联系。现实中的教育、社会地位等因素致使他已无法和莉莉相互理解,历史与现实的脱节带给他一种虚无感。这种虚无感促使他修改了自己的演讲稿,“担心他的听众会理解不了”[2],并将一直伴随着他直至演讲的那一刻。
第二段冲突发生在宴会中与爱佛丝跳四对舞的过程中。从爱佛丝的装饰和言辞中可以看出,她代表着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佛丝的质询使得加布里埃尔对当下这个“思想受折磨的年代”[3]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又一次修改了讲稿:“而我们周围正在成长的新的一代,虽然非常认真并受过高等教育,在我看来却缺少这些美德。”[4]这便是他对爱佛丝的回应与批判,他认为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恰恰背离了民族。值得注意的是的爱佛丝早早离开了宴会,并没有听到加布里埃尔的演讲,这种“激进”也是短暂的。
加布里埃尔同时认为“他的姨妈只不过是两个没有学识的老太太,他担心什么呢?”[5],可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是分离的。“如果我们总是忧郁地陷入这些回忆,我们就没有心思勇敢地继续我们生活中的工作。”[6]尽管从历史沿袭下来的民族精神值得肯定,但现实并没有很好的继承它,历史也同样地难以跟上现实的步伐。历史与现实的割裂致使加布里埃尔企图用空间性的办法解决时间性的困惑,他拒绝了爱佛丝西行之旅的邀请,而是选择“流亡”,向更广阔的世界寻求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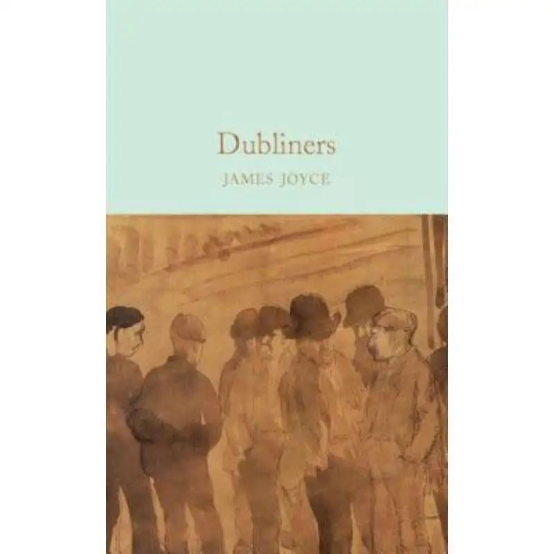
格丽塔是加布里埃尔在现实生活中的映射,事业、爱情与家庭都代表着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美好。宴后散步时,望着格丽塔的背影,他又一次回忆,与历史产生联系。“他渴望对她回忆那些时刻,使她忘记这些年他们在一起的沉闷生活,只记住他们那些销魂的时刻。”[7]这种联系是选择性的,是简化的。他所“筛选”的那些回忆,仅仅是为现实的欢愉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是徒然的。死者迈克尔弗瑞的出现“仿佛在他希望获胜的时刻,某个无形的、蓄意报复的幽灵跟他作对”[8],使加布里埃尔最终不得不直面真实而又完整的历史。“原来她生活中有过那么一段浪漫故事”[9],“现在想到他这个丈夫在她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10],他对现实中的自己感到羞愧。可“那已不再是迈克尔弗瑞为之慨然殉情的脸庞”[11],历史无法更改,如何看待现实并走向未来?加布里埃尔陷入了这一自我拷问。他开始回顾,“也许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12],由散乱的衣服和靴子回顾刚才的“躁动”,又回顾到晚宴、演讲,饮酒和跳舞。接着又想到了 “不久茱莉亚也会变成一个幽灵”[13],“是的,那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14]。最终通过生死的轮回使得历史和现实衔接了起来,并形成了有效联结。
这三段冲突一方面在精神上连续冲击着加布里埃尔,促成了他最后的某种“主观顿悟”。另一方面,他与三个女人的“联系”也不断加深,从开始与莉莉的瞥视与寒暄,到与爱佛丝被动的调情,再到最后对格丽塔主动的“情欲释放”,这期间还伴随着自我的逐步解放。由此,莉莉、爱佛丝与格丽塔与加布里埃尔才更为贴合前文三女神与帕里斯的意象。文末处提到,“他从未觉得自己对任何女人有那样的感情,但他知道,这样一种感情一定是爱情”[15],是加布里埃尔对前两者的否认,说明格丽塔背后所象征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联结”才是这部“思想史”的最终落脚点。
二. 生与死、爱尔兰与世界、历史与现实
“死亡”的氛围贯穿全文。除去提到的多名死者:加布里埃尔的父亲、祖父,玛丽简的母亲,格丽塔旧日的情人;一些隐晦的死亡象征:修士的棺材,《罗密欧与朱丽叶》、《让我像士兵一样倒下》等艺术作品外;更主要的“死亡”是一种循环往复,一成不变的气氛下的麻木与瘫痪。莫肯家的聚会就具有这种“死亡特征”。它每年都办,加布里埃尔的演讲、弗雷迪醉醺醺的到来、莉莉忙前忙后、四对舞、华尔兹、鹅肉与布丁。正如加布里埃尔祖父的那匹马绕着雕像一圈又一圈的跑一样,已没有向前走的打算,“真让人费解”[16]。相反,迈克尔弗瑞这个死者反而能搅乱生者平静的生活,死者尚存而生者已近乎消逝,爱尔兰就是这些生者与死者共享的世界。

时间勾连着生死与爱尔兰。时间的停滞近乎死亡,时间的运转也使得爱尔兰成为了共同体。在时间这条主线背后,是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与“生死”两大问题的思考。一纵两横的三条脉络构建起了《死者》的思想框架。三者在结尾的大雪中汇合。雪的联结首先具有时间性,同一了历史与现实,包含了三十年如一日不断重复的历史,“圣诞节地上没雪就不是真正的圣诞节”[17]。在这样的历史虚无中,人人都“无一例外”地患了感冒。但雪也体现着加布里埃尔对现实的期许,“雪会积聚在树枝上,会在威灵顿纪念碑顶上形成一个明亮的雪帽,在那里一定比在晚餐桌上愉快多了。”[18]“那里空气纯净。远处是树上压着积雪的公园。威灵顿纪念碑戴着一顶闪光的雪帽,耀眼的白雪覆盖着西边十五亩地的原野。”[19]可以说,窗外的雪是加布里埃尔在这场死气沉沉的宴会中所向往的“出路”。“三十年没下过这样大的雪”[20],康奈尔桥的雕塑上,曾经仅仅落在“马”上的雪,也积聚在了“人”的身上。经历了由白马到白人的转变,驾驭着马的人今日能否走出循环往复的怪圈呢?雪在空间上同样具有联结性,“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21],爱尔兰因雪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最后,雪也联结了生死,“落在生者与死者身上”[22]。雪覆盖了一代又一代生者和死者,也将这样继续下去。在雪面前,生与死的交织融会达到了顶峰。
文末,作者又提到了西行——这个宴会中爱佛丝提出的概念。西行是一次复杂的尝试,它蕴含着走向妻子的历史;走向民族,“与爱尔兰保持接触”[23];也是通过死去的迈克尔弗瑞走向死亡。“最好在某种激情全盛时期勇敢地进入那另一个世界,切莫随着年龄增长而凄凉地衰败枯萎。”[24]加布里埃尔睡意朦胧的时候,“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25]。这之后,便应该是苏醒与未来。

高靖涵同学
注释:
[1]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王逢振译. 都柏林人[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第189页。
[2] 同上,第190页。
[3] 同上,第212页。
[4] 同上,第202页。
[5] 同上,第202页。
[6] 同上,第212页。
[7] 同上,第221页。
[8] 同上,第227页。
[9] 同上,第229页。
[10] 同上,第229页。
[11] 同上,第229页。
[12] 同上,第229页。
[13] 同上,第229页。
[14] 同上,第229页。
[15] 同上,第229页。
[16] 同上,第216页。
[17] 同上,第219页。
[18] 同上,第202页。
[19] 同上,第211页。
[20] 同上,第219页。
[21] 同上,第230页。
[22] 同上,第230页。
[23] 同上,第199页。
[24] 同上,第229页。
[25] 同上,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