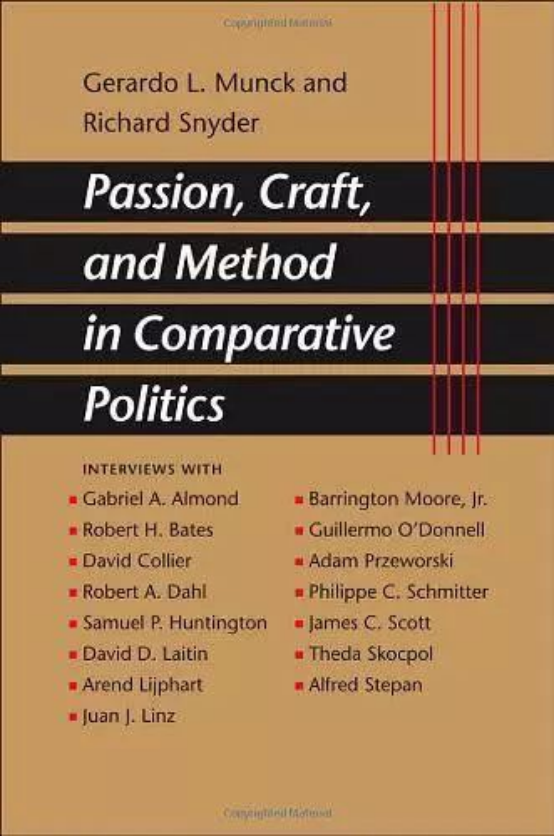译者的话
这篇问答节译自Order and Conflict in Global Perspective,原载于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后者是一本采访的合集,作者采访了十五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其问题关乎五个方面(智识的成长与训练;主要作品和思想;研究的技艺和工具;同事、合作者与学生;比较政治的过去与未来),意图展示比较政治学研究(或更广义的学术研究)背后更人性化的一面。
节选部分中,亨廷顿讨论了他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学术技艺(包括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中的规范性考量),并给出了他对“政治学”(politics)作为一门“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理解。篇幅不长,内容通俗,对亨廷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一下,相信多少能有所启发。
上次翻译亨廷顿的文章是半年前了。那时候,我在欧树军老师和刘晗老师的课上第一次见到美国政治与宪政的“真模样”。借着举办亨廷顿去世十周年学术研讨活动的契机,重新翻看旧日读过的文章,确有相当不同的感受。
寒冬将至,以此追忆那段自由而难忘的日子。
—— 马峻(新雅书院2016级PPE专业学生)
全球视野下的秩序与冲突
受访者:Samuel P. Huntington
采访者:Richard Snyder
采访日期:2001年5月31日与6月11日
采访地点:Cambridge,MA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又颇有争议的政治学家,著有《军人与国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等。
研究:核心观点及其理解
Q:你的研究横跨政治科学的三大主要领域,这是它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你是一位研究美国的学者;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转向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研究,著有国家安全相关的作品;最终,你转向了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出版了Political Power:USA/USSR(Brzezinski and Huntington 1964)。之后你继续横跨三个领域发表作品。
A:我没有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wandered around)。本科阶段,我在耶鲁修习国际关系。研究生阶段,我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修习,主要研究美国政治。之后我转向了军—政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和安全问题(Huntington 1957,1961,1962)。在与布热津斯基合著时(1964),我进入了比较政治学领域。然后我展开了对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研究。现在我每年开一门课,或是有关美国政府(American government),或是比较政治学,或是国际关系。
Q:你是否推荐这种宽领域(wide-range)的进路?
A:不一定。每个人不一样,而我是在领域间徘徊。但其他人开辟并精耕于(carve out)一块领域成了专家。我自己没有真正精深的专长(specialty)。
Q:四处徘徊、并没有特定领域的缺点有哪些?
A:你不会与特定group或club有较深的关联,并且不会成为某一主题(subject)的专家。如果你在不同领域发表作品,某一领域的专家一般不了解你在其他领域的建树。想到我时,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会想起《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和《第三波》(Huntington 1991),但他们根本不了解《军人与国家》或有关美国政治的著作(Huntington 1981b)。这一有趣现象反映出政治科学的分化与专门化程度。我喜欢提出于我而言重要的问题——它们对现实世界和学界都重要。因此,我会跟循这些问题(questions and issues)所在的路径,即使这要求我转换研究领域。
Q:你觉得自己最棒的想法(idea)有哪些?
A:我的第一本书《军人与国家》(Huntington 1957)讨论的是军人职业的本质(nature),即客观与主观文官控制(civilian control),而这些观点在45年后仍被持续地争论、质疑和使用。显然,我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中提出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处观点尤为如此:如果没有伴生发展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变迁会如何引发政治衰败。它无疑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且有许多研究试图在不同情境下检验那些命题。
Q:在你看来,为什么《变化社会》中的观点会变得流行(caught on)?
A:我以相当简明的方式提出了命题。它们是一系列人们能把握和适用的假说。
Q:“变化社会”与“政治秩序”有怎样的关联?……
A:……现代化理论讨论的是经济—社会变迁和发展,我的书显然与此相关。总的看法是这些过程可能对政治不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或暗或明的看法都假设现代化多元一体(all of one piece):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因此经济条件的改善必然带来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
Q:你还有其他尤为引以为豪的观点吗?
A:在我看来,《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Huntington 1981b)对有关美国政治本质(nature)的讨论有所贡献。它从基本的托克维尔的理论出发,阐发了路易哈兹(1955)对美国社会价值层面的强烈共识的论述,并进一步说道:“没错,这是对的,但实际上这一共识解释了我们社会中时而出现的不稳定和冲突。”我觉得这对理解美国政治的变迁有所助益。
Q:你有哪些想法或作品曾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或被误解过?
A:它们都被误解过。
Q:你曾说你努力地在作品中明晰地陈述事情。那为什么你的观点会遭到误解呢?
A:表述明晰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人们常将自以为是的想法带入作品。比如说Carl Gershman,他曾写过一篇对《文明的冲突》的书评,其中多次提到我对伊斯兰世界的断言,即我将它称为一个“单一体”(monolithic entity)。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在书中反复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分化(divisions)。……不知为何,人们以为亨廷顿在思考文明,并将文明看作是单一的、整全的实体。事实并非如此。但这就是许多人对这本书所做的批评之一。
Q:这种看法将你的作品解读成了“桌球现实主义”(billiard ball realism)。
A:是的。事实上很多人明确地说《文明的冲突》是最新版的桌球现实主义,虽然它讨论的是文明而非民族国家。
Q:人们将《文明的冲突》解读为一部悲观的作品。与此相反,因为《第三波》关注的是民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所以它时常被视为一部充满希望的、乐观的作品。
A:我不同意这一点。这两本书处理的是不同的主题。《第三波》有一整章讨论逆民主化浪潮和民主巩固的问题(Huntington 1991,Ch.6)。它本质上研究的是三十多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s)为何且如何出现在了20世纪70、80年代,但书中绝不曾有对民主化必然延续的极端乐观。我小心翼翼地指出了进一步民主化的困境——文化的、经济的及其他。并且我讨论了新生民主政权在巩固民主时面临的困难。
Q:“第三波”结束了吗?
A:在一个较宏观的视野看来,是的,它结束了。这一现状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将不会再出现。但20世纪中期出现的、通向民主的一系列变化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它们经济上、文化上有适合民主化的条件,并且都受到美国或西欧国家的影响。拥有上述三种因素的那类国家几近消失。这是民主化放缓的原因,也是以选举为形式的对民主程序的引入,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之间存在间隔的原因。……
Q:你觉得自己是否有作品被忽略了,或没能得到应得的关注?
A:我希望《失衡的承诺》能在之前获得更多关注。
研究的过程、问题的选择
Q:公共问题和当代事件显然影响了你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你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
A:它可能不是政府或公共机构都关注的那类“公共”问题,但我想审视的是现实世界中正发生的事情,即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政府或政治中的有趣问题。比方说,我对军—政关系感兴趣,是因为杜鲁门炒掉了麦克阿瑟,所以军—政关系看上去很重要。我发现周围没有多少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可能之前15至20年间出过两三本还比较严肃的书。所以我说,“在这个有趣的领域中,存在着关乎军政关系的重要的、尚未回答的问题”(Huntington 1957,1962)。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人们都在讨论现代化和发展时,当我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时,我看到的是混乱、无政府和腐败。因此我想,“让我们观察得稍微更仔细些吧——那里存在的更多是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因此我写下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
Q:你并不只是想当反对派?
A:是的。但拾人牙慧也没什么意思。如果你不能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或理论(它们不一定相反),那么就没多大价值。
年轻时的亨廷顿
Q:在写《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你说你向外观察到的世界有着暴力、不稳定、衰败和失序。为什么其他人没看到此番图景?
A: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事情正如他们所愿地发生着。但仍有人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来观察那些发生在第三世界的事情。
Q:你所谓的“向外观察世界”(look out at the world)是什么意思呢?你如何落实它?
A:你会读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Q:只是阅读吗?或者你会与他人交流和互动?哈佛显然不缺有趣的访问者。
A:当然。但我主要靠阅读。
Q:选定研究对象后,下一步你会怎么做?
A:我会试着更多地了解它,思考它,形成对它的观点,然后设计出一条理论进路或一套理论框架。你会阅读材料,看看其他人说过什么,试着了解更多东西,然后进行思考。
Q:方法论工具在你的研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A:我不会过多考虑方法。我不会有意寻求或定义一种方法。一般来说,我会试着研究一个主题,并围绕它形成我所谓的“经验性概括”(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这当然包括进行对照的尝试。
Q:你不是一位“小规模样本”(small-N)的比较研究者,不会纠缠于三或四个案例并试图进行深挖。你似乎更像一位“中等”或“大规模样本”的比较研究者。对此你是否同意?
A:我想是这样的。……当你提到“大规模样本”时,我想到的是有130个案例的复杂计量研究。我对这类工作并不反对,但我不属于此类。
Q:在一些人看来,一流的比较研究者深谙一国政治的运行方式,因为这为他更广阔的归纳提供了坚实基础。对此你是否赞同?
A:我对此表示怀疑。就一国政治来说,我比较了解的只有美国。但我不觉得它对我更广的归纳有很大助益。
Q:历史分析在你的研究中扮演了怎样得角色?
A:你需要依靠历史,因为你研究的是经验(experience)。历史即人类的经验。你得处理历史材料,并探究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如我所说,政治学家所做的就是对历史进程的归纳。当然,对此有不同的做法。
Q:你对田野调查怎么看?
A:我不相信它!
规范性考量(normative concern)与科学
Q:你的研究是否会受规范性考量引导?
A:几乎所有人的研究都有一个规范性的起点。人们会关心某一个特定问题:不平等、不公正、推进民主的渴望。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它是推动学者进入特定主题的动力。
Q:但据于某些对科学的理解,研究者不放任规范性议程(normative agenda)影响他们的研究。
A:科学家们研究什么?在物理和生物科学中,他们通常只是试图更好地理解宇宙。但许多科学研究被这样一种观念驱动: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能帮助人类。
Q:你是否自视为一位科学家?
A:并不。“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暗含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我自视为一名学者(scholar),而非科学家。
Q:但我们的领域被称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
A:我知道,这很不幸(unfortunate)。
Q:你是否自视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A:我抵制并反对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它意味着一类人:大谈公共事务并参与深奥的智识争议。我不视其为一种褒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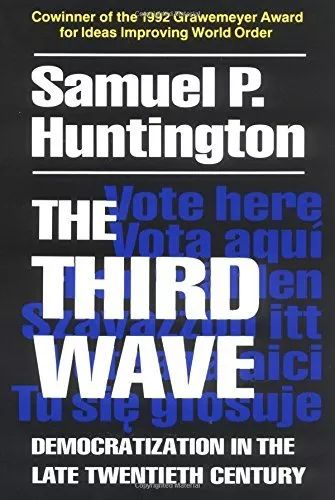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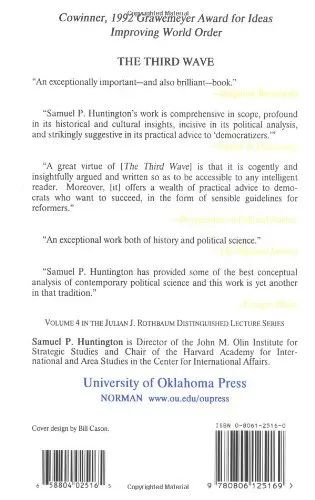
Q:你的一些作品,比如《第三波》,会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的确,在《第三波》封皮上的推介中,布热津斯基将你描述为一位“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你是否有意力图生产与政策制定者有关的作品?
A:任何对真实世界问题的严肃研究都暗含政策意图。实际上,这对我所有的作品都适用。我的第一本书《军人与国家》无疑有着含蓄的——事实上是相当直白的——有关如何掌控军—政关系的观点。书中没有探讨政策的一章,但我觉得其中的政策意图相当清楚。正如我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前言中所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因为我关心政治秩序,以及已实现政治秩序并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