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8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主办的“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系列活动的第一期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古希腊戏剧中的自然与文明”为主题,围绕有关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欧里庇得斯《伊翁》与阿里斯托芬《云》的三篇报告及其评议展开。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甘阳、李震、颜荻,法学院赵晓力,以及北京大学王铭铭、张辉、谷裕、渠敬东、吴飞、陈斯一,中国社科院贺方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黄薇薇等老师相聚在云端,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一、开幕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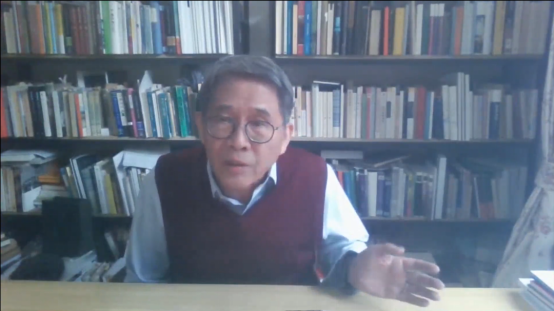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甘阳老师
作为“新雅·古典学工作坊”系列活动的总策划,甘阳老师首先作了开幕致辞。他谈到,本期讨论的主题“自然与文明”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当前疫情对正常生活的打断正暴露出我们已经生活在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关系当中,例如本次会议因疫情而一再被推迟。学术活动毫无疑问是人类的文明活动,然而这一文明活动已经一而再、再而三遭受到强大的自然力的打断、威胁和破坏,说明人类并非生活在完全人造的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而是始终处在自然环境之中。新冠病毒这种“自然”,就特别能体现西方传统的或者主流的对自然的理解,即,自然归根结底对人类是不友好的,即使从最好的方面说,也最多是无动于衷。
这种理解当然也隐含了对人性自然(human nature)的理解:虽然文明都是由人所创造的,但是人性自然本身始终包含着文明无法驯化、无法控制的东西。现代(20世纪)以后,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无论是“力比多”还是“死本能”,都是这种无法被文明化、或是抗拒文明化的东西。
这引出第三个问题,既然所有的文明都是人所创造的,但人性本身是并不完美的、甚至是丑恶的东西,那么人所创造的文明本身也可能并不是那么美好,文明本身就隐含着这种丑恶和暴力。他认为这可能是“自然与文明”至少从西方的脉络里面隐含的一些问题,和中国的理解可能不同。
弗洛伊德在20世纪的第一年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回到古希腊悲剧,恰恰是点出了人的本质所在,隐含着人类文明所无法摆脱的东西。不管今天我们多么的现代,这些问题仍然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思考人的本性抑或文明的本性,古希腊的问题,特别在悲剧中所体现的这些问题,都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
二、报告与评议
接下来的引言报告及评议环节,由赵晓力老师主持。第一场,由陈斯一老师作《<安提戈涅>的自然与习俗问题》报告。



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斯一老师
陈斯一老师首先综述了对《安提戈涅》的两种传统读法:亚里士多德“自然vs习俗”与黑格尔“家庭vs国家”的框架。他主要针对亚里士多德,辨析了“自然正义”的文本依据不足,希望重新探讨既有的解释框架。
陈老师的解读,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有关“自然和文明”对立的基本框架,但在具体的冲突点上不认同上述两者。陈老师认为,更深层次的冲突隐藏在两个人物内部,无论是安提戈涅捍卫家庭或是克瑞翁捍卫城邦,他们的捍卫都基于自身人格的强力,这种人格力量本身和他们所要捍卫的共同体原则之间形成强大的冲突,乃至不可化解的张力。而他们内部的冲突在戏剧中则外化为安提戈涅与伊斯摩涅、克瑞翁与歌队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伊斯摩涅和歌队才真正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原则和国家原则的精神。
对于克瑞翁的分析,陈老师继而将故事背景解读为由内战引发的从政治状态退回到自然状态的危机。歌队的态度是希望尽快从自然状态返回到政治状态,但克瑞翁拒绝忘记,这两者形成鲜明对立。他不愿意仅仅凭借法理登上王位,而且希望凭借自己的灵魂品性和判断配得王位,所以他拒绝现成的政治秩序,希望抓住并利用自然状态的危机对自身政治品性进行考验。克瑞翁要用其个人的自然强力来克服这个自然状态。所以,他才需要根本性的立法来重建一个秩序:首先通过区别对待两具尸体,划分敌友,从自然中建立分别;其次要求全体公民服从法令,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陈老师提出,克瑞翁这种人格的自我诉求根本上与安提戈涅是非常相似的,安提戈涅也希望在一个重大考验之中成就自我欲望。首先,安提戈涅对葬礼的要求不完全代表自然,而恰恰代表古希腊最根本的埋葬尸体的礼俗,目的在于安顿文明对自然的秩序。其次,在辩论中,伊斯摩涅着眼于人在世界的命运位置和相应的规范。她认可既定的秩序,接受在服从的前提下行动。但安提戈涅将其视作一个展示本性高贵与否的机会,并主动地将这个问题原则化甚至极端化。事实上,安提戈涅对死亡敏感而迷恋,是她“英雄式的生存”的源泉,对于所有英雄而言,都是通过作为、经受考验,去抓住有限的生命,换回一种光荣和不朽。因此,陈老师认为安提戈涅拥有强烈的希腊式英雄主义的色彩,她并非家庭伦理的代表。强烈的自我意识、坚决而顽固的原则感、僭越常理的行事倾向、盛气凌人的自信等等,这些品性与其说是反映了政治或家庭共同体的伦理原则,不如说是反映了英雄人格的一种自然强力。
相应地,“人颂”也是同时针对这两个人的,是对于人性悖谬的一种展现。“人颂”表明自然强力极其危险,因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但是无法征服死亡;同时,在面对共同体时,人最终要征服的是人性自身,即学会在城邦中生活,但这与其“胆大妄为”的自然强力本是自相矛盾的。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张辉老师
在其后的评议中,张辉老师充分肯定了陈斯一老师在承续黑格尔框架下做出的重要突破,并认为将悲剧置于史诗背景下的理解(安提戈涅-阿基琉斯,伊斯墨涅-奥德修斯,克瑞翁-赫克托耳)颇有趣味,也更丰富了我们对古希腊自然观的认识。自然与习俗的冲突,既存在于家庭与城邦的对立之上,也更存在于个人、特别是超群个人身上。他同时提醒到,在借用黑格尔式冲突论的同时,或也可以注意康德式的崇高论对形而上学之维的关注,应特别注意全剧结尾歌队长对虔敬的再次肯认。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颜荻老师
第二场由颜荻老师报告《欧里庇得斯<伊翁>中的公民身份问题》。颜荻老师首先说明了“公民身份”与“自然与文明”问题的相关性:赫西俄德《神谱》展现出自然本身不构成秩序与文明的基础,相反,以宙斯吞噬墨提斯生出雅典娜这一“反自然”的生育为例,宇宙秩序始于强烈的建构乃至对自然的压制和打破的基础之上。这一“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感构成了此后希腊人思考该问题的基本视野。到古典时期,雅典利用“地生人”神话,试图以“非两性生育”、从起源上排除女性的方式构建男性掌握生育权进而男性至上的社会秩序原则,这本质上是想象了一种新的“自然”,重新将文明建立在“自然”之上。但这种对自然的再定义以及将文明建立在打引号的“自然”之上的做法在欧里庇得斯看来问题重重,《伊翁》一剧正是对此问题的探讨,它承接了“地生人”神话,回应了古希腊思想中有关文明与自然关系的问题。
简要介绍《伊翁》的故事情节后,颜老师提出,戏剧所呈现的是一个后“地生人”的、两性生育的时代,此时雅典公民权的获得要求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且是合法夫妻,这虽然看上去是反“地生人”的生育模式,但它实际却是对“地生人”原则的贯彻,因为,男性牢牢通过婚姻这个文明的制度掌握了生育权,这从根本上讲是对女性作为生育的自然主体的一种打破。作为私生子的伊翁,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因此,整部剧的核心主题,就是拯救私生子,即,将一个原本不可能成为雅典公民的非法生育的孩子送回雅典,让他获得雅典公民的身份,甚至还让他成为雅典未来的最高的统治者。从结局来看,这一目标达成了,雅典夫妇克瑞乌莎和克苏托斯最终认伊翁作子并赋予了他公民身份。
问题在于,既然结局如此,为什么阿波罗不直接同时告诉克瑞乌莎和克苏托斯两人伊翁就是他们的孩子,而是要冒着情节拖沓的危险让伊翁与两人分别相认呢?学界传统的解释是,这呈现了伊翁几次三番的“死亡”与“再生”。而颜老师认为,伊翁所经历的几次身份的改变,才是这个“死亡”与“再生”背后隐含的更为根本的意义,即:伴随着每次的死亡与诞生,伊翁其实获得了文明世界当中不同的身份,因此探究剧中伊翁身份的转变十分重要。
欧里庇得斯其实提出了好几种伊翁获得身份的可能性,由此试验其成效。在此之中,最关键的,是伊翁单独作为克苏托斯儿子方案。这个方案看似可行但却失败了。这一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剧中的男性,无论是阿波罗还是克苏托斯或伊翁,都小看了克瑞乌莎这个女人,忽略了她是婚姻或者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潜在的力量,所以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复仇。女人复仇的反转为观众提出了重要问题,就是女性的自然力量在婚姻这个文明关系当中是不能被忽略的,人们不能预设文明建构所起的男性权威绝对不会被拥有自然力量的女性所挑战。在后来一种方案中,阿波罗送去祭司揭露了伊翁与克瑞乌莎的真实私生子关系,此时克瑞乌莎成为了唯一一个正面面对并揭露所有真相的人。她扯下了文明的遮羞布,承认了文明原本希望压制或回避的自然的黑暗面。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它也成为伊翁身份建立的一个稳固的起点。最终,伊翁与亲生母亲克瑞乌莎相认,但同时又继续在克苏托斯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认其作父,由此,伊翁拥有了雅典母亲与雅典父亲,从而获得了雅典公民身份。
颜荻老师提出本部戏剧的深刻意义。欧里彼得斯的现实主义叙事表明,文明的延续需要建立在对自然本性的黑暗面的承认,甚至不惜用谎言去维护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欧式可能会认为,文明和自然其实不大可能以任何的方式全面的和解,一方不可能根本上塑造另外一方,当然更不可能被另外一方所征服,文明只能在承认自然永恒张力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自我保存。

北京大学哲学系 吴飞老师
在其后的评议中,吴飞老师高度肯定了颜老师解读《伊翁》的理论意义,并从《伊翁》联想到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故事。同时,吴老师提出,在讨论“自然与文明”时,应当首先明确所谓的“自然”是什么,颜老师文章所讨论的“自然”似乎与乱伦以及性的关联较大,但倘若考虑到母子的联结作为一种“自然”的亲子关系,那么,文本中的自然与城邦习俗的冲突便似乎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烈。此外,倘若引入宗教的维度,《伊翁》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私生子公民权的问题。伊翁作为阿波罗神之子,可以类比于罗马神话中建国国王罗慕路斯(Romulus)作为战神玛尔斯(Mars)之子,在后者故事中,“神之子”为王权赋予了正当性,那么在前者中,伊翁最终成为建城之王,也应与“神之子”的身份相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黄薇薇老师
第三场由黄薇薇老师报告《“女云神”与苏格拉底——兼论阿里斯托芬对自然哲学的批评》。该报告主要讨论喜剧对自然的概念和自然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是何种看法。黄老师认为云的核心主题就是:知识和修辞对于城邦的影响,或自然哲学对城邦的启蒙所带来的危害。
黄老师试图推进解答的是,自然知识到底如何与修辞勾连起来?即,云神处于评价的什么位置?根据文本细节,她提出,云神具有双重性,一个是苏格拉底口中的云神,另外一个,是阿里斯多芬,他塑造的云神。前者回应了知识和修辞如何勾连在一起的问题,后者传递了关于自然爱欲的缺陷和问题的根源的观点。
对此,黄老师提出三处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斯特瑞普西阿德斯是为了诡辩与欺诈而去信仰云神,由此,他以自己的低级的欲望与最高的存在发生关联;第二,云变幻莫测的自然属性,为诡辩的效果提供了依据;第三,苏格拉底用云神取代了宙斯,取消了行动与惩罚的关联,这是自然知识与修辞的三次勾连。因此,自然哲人实际上是用自然知识替换了城邦的宗教信仰,相应地,云神也就被立为了新神。
相反,阿里斯托芬的云神显然与苏格拉底的不同,是一种自然神,而且云神并不是唯一的神。她们参与游行以及所有的节日娱乐,这说明云神比苏格拉底更知道城邦生活的一切,与城邦和人事有所关联。云神承认宙斯,但并不崇拜,这有两方面用意:第一,她要巩固自己在自然方面的存在根基。第二,他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进入和融入城邦神的行列。
由此可见,阿里斯托芬对于自然哲学的真正的态度是,研究形而上学或者自然哲学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推翻城邦的习俗,也不要将自然知识不加区分的随意传授给世人,悬在空中的思想必须降下来处理,自然哲学需要向政治哲学转向。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贺方婴老师
随后,贺方婴老师做了点评。她谈到,黄薇薇老师的报告激发了自己重读阿里斯托芬的兴趣和勇气;受报告“自然知识和修辞的三次勾连”的启发,她认为剧中敬拜云神的苏格拉底可能既不了解云神的physis[自然],也不了解他自己灵魂的physis。换言之,《云》中的苏格拉底既没有真正地认识自然,也没有自我认识,更谈不上为哲学生活本身辩护。这可能是保守主义者阿里斯托芬对于青年苏格拉底最尖锐也是最真诚的批评。毕竟,在柏拉图的《斐多》中苏格拉底也承认自己年轻时对探求自然知识饱含热望。《云》于公元前423年上演,而柏拉图则将《会饮》的故事安排在《云》上演7年之后,柏拉图笔下的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在这场会饮中一直保持清醒,直至结束,这些戏剧情节设计或可视作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对《云》批评的重视与回应。政治哲学转向后的苏格拉底要面对城邦的各种意见和批评,相形之下,他可能更为重视来自喜剧诗人出于友爱的批判——在尖锐的嘲笑中包含某种危险的真相,这既是诗人对哲学生活的理解和认同,也是关于友爱政治的教诲。喜剧诗人与政治哲人都需要直面来自城邦的指控。最后,贺方婴老师就黄老师主持翻译的阿里斯托芬译文提出了具体的问题。
三、圆桌讨论
在圆桌讨论环节,甘阳老师首先对前三场报告作了总体的点评与回应。甘老师认为三场报告都非常精彩,将“自然与文明”问题彼此关联地凸显出来。甘老师对陈斯一老师的总体思路表示赞成,即摆脱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悲剧解释传统,将安提戈涅看作是自然对文明的一种僭越;同时甘老师指出陈老师似乎有将悲剧向荷马史诗方向解释的倾向,这值得再商榷。随后,甘老师指出《伊翁》应是西方文学中第一部关于私生子的剧,“私生子”恰恰凸显出自然与文明的问题,尤其是文明的荒谬之处。《伊翁》剧中的层层掩盖体现出希罗多德已经隐含的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任何文明是真正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这牵涉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真正的“自然法”究竟存不存在?另一方面,乱伦之所以成为重大的问题,乃因为亲属关系之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因此乱伦禁忌究竟是自然的还是人类的选择,就有待澄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铭铭老师
随后,王铭铭老师回应了几个报告和甘老师提出的问题。王老师指出对《伊翁》的理解可以进一步关注“王”的诞生的双重逻辑:王介于王冠的必然性和身体的有死性之间。此外,王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他指出,人类学从1850-1900年划分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进程,他追问这样一个19世纪划分“自然与文明”的论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运用来谈论古希腊社会?这种讨论是否已经建立在进化论之上?其次,他认为这次讨论所解读的文明与自然,都是站在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与自然,那么,是否可以站在抽离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与自然本身?因此王老师最后提问,我们有没有可能考察古希腊时代的自然与文明的现实状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渠敬东老师
渠敬东老师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依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渠老师指出,黑格尔以“直接的伦理性”和“真实的精神”解释古希腊的伦理世界。“直接的伦理性”意味着在古希腊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概念。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古希腊的实质构造,即人法和神法的规定之中考虑悲剧的问题。而“真实的精神”意味着“死亡”成为人之界标的根本性,悲剧时代的人需要以神法(冥界)为依托的家庭来安葬。悲剧正是在这样神法和人法的层层推动下复杂交融,直至最后的裂解。
讨论过后,报告的三位老师也依次进行了回应。陈斯一老师回应渠敬东老师关于 “自我”概念的理解,并就人与伦理神法的直接等同提出了质疑;随后也回应了甘阳老师的观点,对“英雄时代”与“后英雄时代”的关系进行了辨析。颜荻老师回应了《伊翁》的“神之子”问题,并与《酒神的伴侣》的“私生子”酒神狄奥尼索斯进行了对比,提出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神之子”更突出的一个面向是其不合法性,尤其《伊翁》结尾中伊翁称王的前提是对其作为“神之子”这一事实的隐瞒,这是非常特殊的关于“神之子”的例子。黄薇薇老师回应了贺方婴老师关于《云》中苏格拉底的道德化问题,以及未在报告中展开的哲人与诗人的爱欲问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谷裕老师
圆桌讨论的最后,主持人谷裕老师提出:本次工作坊主要围绕关于“人”的“自然与文明”的解读,是否还能更细致地探讨古希腊世界“神”的存在及其秩序?甘阳老师回应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下面第三场工作坊(主题为“‘神’观念与早期中国思想”,6月11日举办)会从中国方面触及神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西方的神的问题的考虑。


与会者线上合影
期待老师们早日线下相聚,也期待接下来的“新雅·古典学工作坊”顺利开展。

纪要整理:杨琦 刘宇薇
审 核:张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