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1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和北京大学政经哲学社联同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高校政经哲专业论坛”。新雅书院副院长赵晓力老师在该论坛上作了主题演讲:《阿德曼托斯的教育》。以下是演讲全文。

赵晓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新雅《政治哲学》《法律与文学》任课教师
我相信在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政经哲专业的同学中间,《理想国》都是被广泛阅读的一本书。我看最近这次“政经哲杯”书评比赛中写《理想国》的就挺多的。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只能简单讲一下我对《理想国》中一个人物——阿德曼托斯的理解。
《理想国》第一卷,苏格拉底依次和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对话;从第二卷开始,是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兄弟俩的交替对话;如果第一卷结束时正是晚餐时分(352b,354a),那么第二卷之后,用阿德曼托斯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日落之后的火炬接力赛马”(328a)——只不过是在玻勒马霍斯家里,用言辞进行的。两个“接力者”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历来被关注最多的是格劳孔;许多读《理想国》的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格劳孔——如果不是代入苏格拉底或者色拉叙马霍斯的话。今天为什么讲阿德曼托斯呢?因为对于政经哲的教育而言,阿德曼托斯这个人或许更值得关注。
一、阿德曼托斯其人
在柏拉图三十五篇对话中,阿德曼托斯共出场三次。从对话的戏剧时间看,依次是《理想国》、《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巴门尼德》的框架对话。《理想国》中的阿德曼托斯似乎还年轻,这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前431-前404)某一次麦加拉战役之后,阿德曼托斯、格劳孔兄弟刚刚在这场战役中出名(《理想国》368a);《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前399雅典公审苏格拉底的法庭,苏格拉底明确说阿德曼托斯在场;《巴门尼德》的框架对话的戏剧时间是前382,此时苏格拉底已弃世19年。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针对败坏青年的指控,苏格拉底说,如果他真的曾经败坏过一些青年,这些人长大了,意识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曾被我败坏过,那他们自己就会来控告我;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来,那他们的父、兄也会来(33d)。随后他一共提到两组共十四个人,前三组是父子关系,后四组是兄弟关系。

出面控告苏格拉底的三个人不在这个名单上。苏格拉底的言下之意是说,这是一场公诉,而非私诉,控告者其实是雅典城邦,不过这并不是今天的主题。
仔细看一下这两组人物会发现,右边这一组可能被苏格拉底“败坏”过的七人,除了Theodotus和Theages已经去世,还有四人又都出现在《斐多》中,他们见证了苏格拉底之死;这四人自然不会出面控告苏格拉底的;唯一的例外是柏拉图,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在场,但苏格拉底饮药而死的时候却不在,据说是病了。这一点值得玩味,但也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阿德曼托斯。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
苏格拉底在这里提到阿德曼托斯是说,假如我真的败坏过柏拉图,那么柏拉图本人悔悟后会来告我;即使他不来告我,那么他的兄长阿德曼托斯也会来告我。现在看一下左边父、兄这一组会发现,七个父、兄的名字在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中出现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克里同,一个是阿德曼托斯。克里同是苏格拉底的乡党、同龄人、发小;但是从《克里同》、《斐多》这些对话中我们知道,克里同从来只关心苏格拉底的身体(《斐多》),而苏格拉底试图跟他谈灵魂的时候,他是听不懂的(《克里同》)。
这样一来,阿德曼托斯就很尴尬了。我们知道在《理想国》中阿德曼托斯是被苏格拉底“败坏”过的,但是他现在却和那个从来没有被苏格拉底“败坏”的克里同放在了一起。担保苏格拉底30个米纳罚款的四人名单中也没有他(这四个人是柏拉图、克里同父子和Apollodorus,《苏格拉底的申辩》38b)。柏拉图也许是想让我们看到,《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阿德曼托斯的教育,到底结果怎么样。
回到《理想国》。我们知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阿德曼托斯促成了《理想国》这场对话。当玻勒马霍斯强迫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留下来的时候,阿德曼托斯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说在日落之后会有一个马背上的火炬接力,苏格拉底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格劳孔则同意留在比雷埃夫斯港,才有了这一场彻夜对话。
在第二卷中,在言辞建城的时候,首先和苏格拉底对话的也是阿德曼托斯。最小的城邦也必须有四种技艺,照料人的食、住、衣、行;提出这四种技艺后,苏格拉底给阿德曼托斯一个选择:是每个人只专门干一件事,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彼此满足大家的需要,还是每个人都干四件事,自给自足?我们看一下370a的翻译。据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李圣乔同学(他学过古希腊语)的考证,从字面上讲,英译本中剑桥本的翻译是最接近原文的:阿德曼托斯说“另外一种更容易些”。但“另外一种”究竟指的是第一种分工模式,还是第二种自给自足模式,字面上看不出来。布鲁姆1968年英文版中,阿德曼托斯说的是“分工”更容易些;到了1991年第二版,则改成了“自给自足”更容易。根据前后文判断,布鲁姆第二版译文可能更接近阿德曼托斯的本意,尽管这个本意很含糊。阿德曼托斯当然知道,人人都自给自足,没有和他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不可能有城邦;但同时他又说,一个人自己干这四件事对他自己更“容易”——他似乎更倾向于一种自足的、自己照料自己全部身体需要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阿德曼托斯更像一个古代的鲁滨逊,未必是一个天生的城邦的动物。
苏格拉底说人生来各不相同,不同的人适合干不同的工作。阿德曼托斯在苏格拉底的劝说下重新选择了“分工”,这使得言辞中建城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那我们来看一下阿德曼托斯适合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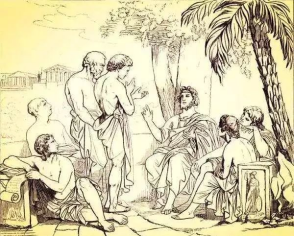
四种直接照料身体的技艺之后,又产生了第二批技艺或者职业。第二批职业包括木匠铜匠这些手工业者,和牧牛牧羊的牛倌羊倌。这些技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照料人的身体需要——养牛养羊并不是为了要吃它们(吃肉并不是人的自然需要),而是让农夫和建筑师有牛耕地拉车,让纺织工和鞋匠能够有牛羊的毛和皮作原料,也就是说,第一批技艺产生了对第二批技艺的需求,第二批技艺服务于第一批技艺。
这个逻辑扩展下去,又产生了服务于第一、二批技艺的第三批技艺或职业,一种是做海上城际贸易的商人,一种是城内市场上的小店主,还有一种是雇工。苏格拉底和阿德曼托斯所建的“健康城邦”,一共有九种技艺或职业。——这时克法洛斯已经离去,在座的除苏格拉底之外,正好是九个人。在这九种技艺或者职业中,阿德曼托斯会选择什么呢?
是第八种:小店主。阿德曼托斯说,身体最弱干不了其他的那些人,会去做一个小店主。“他们待在市场上,从需要卖东西的人那里买,为了钱;卖东西给需要买的人,也是为了钱。”(371c-d)。第八种职业,城邦之间的海上贸易商以货易货就可以,而在城邦内的市场上,大家耗不起以货易货的时间,于是就产生了小店主这种职业。他以钱易货,第二天再把收的货卖给需要的人。要让卖东西、买东西的人都认可你的钱是钱可不容易,小店主其实还扮演了健康城邦银行的角色。第九种职业雇工用力气换钱,适合于有力气但头脑不大灵光的人。阿德曼托斯则相反,属于头脑灵光但身体弱的那种人。和雇工不一样,他不光挣钱,还保管钱;他是小店主,也是钱商。
谈到钱,我们回头看看《理想国》第一卷里面涉及钱的对话。实际上,无论是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还是色拉叙马霍斯,苏格拉底和他们的对话中都谈到了钱。色拉叙马霍斯本来就是来雅典挣钱的,和苏格对话之前要先把谁出钱的事谈好。他对正义的定义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苏格拉底说,如果用技艺类比正义的话,每一种职业,比如说医生,都运用两种技艺,其中医术本身是照料身体的,它服务于对象——“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医生的利益,只有医生的挣钱术才符合医生的利益。这毋宁是说,如果“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说法正确的话,那么色拉叙马霍斯其实是个挣钱大师,这不是自命不凡的修辞学家色拉叙马霍斯所能接受的。所以他在第二次论证“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时候只好放弃了挣钱。但苏格拉底依然用牧羊术类比战胜了他:严格意义上的牧羊技艺考虑的也是羊的利益,而非羊倌或羊主人的利益。
在“健康城邦”中我们看到,并非所有的技艺都伴随着挣钱术,只有阿德曼托斯喜爱的第八种“小店主”和第九种雇工两种职业,才会用到挣钱术。前七种技艺,都无涉挣钱。
不过,阿德曼托斯理想的小店主,不光挣钱,还保管钱。在这方面他更像克法洛斯,而不是色拉叙马霍斯。克法洛斯的祖父,把继承的财产翻了好几番;克法洛斯的父亲,挣钱不行,保管钱也不行,最擅长的是花钱——把家产挥霍到比当初克法洛斯的祖父继承的还要少的田地;经过克法洛斯本人的努力,才把这份家产恢复到祖父刚继承时的地步——或许还要多一点。(330b)看来,克法洛斯本人在挣钱方面虽然比不上自己的祖父,但在保管钱方面则比自己的父亲强。
苏格拉底对克法洛斯的评价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是挣钱的人,所以你也不贪财;挣钱的人最爱钱,就像诗人爱自己的诗,父母爱自己的子女,是因为那都是自己的。这样一个评价也适合于阿德曼托斯:阿德曼托斯是个隐秘的爱钱者,但不像色拉叙马霍斯那么爱挣钱。如今大学里有一个专业叫“经济与金融”,很多家长对它的理解就是“挣钱与管钱”。其实今天的年轻人更喜欢管钱而不是挣钱。因为管钱的人可以天天摸钱,这比父母辈辛苦挣钱爽多了。但正如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谈到的那样,最善于保管钱的人也是最善于盗窃钱的人,这是一个天天摸钱的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看新闻就会看到这一点。
阿德曼托斯要是做了小店主兼钱商,我相信他最喜欢干的事也不是挣钱,而是摸钱。他喜欢容易的事情,摸钱更容易。
二、阿德曼托斯的诗教
看清楚阿德曼托斯是个什么样的人,才能理解《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阿德曼托斯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教育。在395c这个地方,苏格拉底给阿德曼托斯提出了四个德性上的目标:勇敢、节制、虔敬(holy)、自由(free),这和402c那里他对格劳孔提出的目标不同:节制、勇敢、大度(liberality)、高尚(magnificence)。对格劳孔来说,最重要的德性并不是勇敢,而是节制,因为格劳孔已经是一个“勇敢”的人了(357a);而对于阿德曼托斯来说,最重要的德性不是节制,而是勇敢。
对阿德曼托斯来说,勇敢就是要“不怕死”。喜欢干容易的事的人大抵怕苦,怕苦的人大抵怕死。对他的“不怕死”教育从虔敬教育开始。为什么从虔敬开始呢?这要注意阿德曼托斯与克法洛斯的关联。在第一卷里,克法洛斯就是一个怕死的人,他对抗这种恐惧的方式是不停地给神献祭;苏格拉底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献祭完,离开的时候也是要去献祭。在《游叙弗伦》里,苏格拉底通过言辞迫使一心要模仿神的游叙弗伦回到习俗意义上的虔敬,而习俗意义上的虔敬就是像众人一样习惯于祈祷和献祭,献祭就是给神点什么东西,祈祷就是向神要点什么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人神之间的交易。从第二卷中我们知道,阿德曼托斯对这种人神交易很是不满,因为这使得不正义的人也能通过贿赂神逃脱惩罚,不正义。为了要阿德曼托斯“不怕死”,苏格拉底切断人和神之间的交易关系。神只与人事中的好的方面有关。只有完成这种教育后,才能对他进行最重要的教育,即关于勇敢的教育。苏格拉底给他树立的模仿对象不是神,而是荷马英雄阿基里斯,但却是一个经苏格拉底改造过的阿基里斯,一个不怕死的阿基里斯——《荷马史诗》中所有不符合这一形象的描述都被删掉了。这种勇敢教育也是自由教育,自由意味着害怕奴役甚于害怕死亡。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阿德曼托斯的“哭”的教育。既然死不是一件坏事,那么亲友的死亡也没有什么好哭的了。对阿德曼托斯的节制教育,首先强调的要服从长官,阿基里斯不服从阿伽门农的段落都被删掉了——不服从长官并不是勇敢的表现,而是不节制的表现。对欲望的节制,针对的是阿德曼托斯对于金钱的隐秘欲望,阿基里斯爱钱的说法也被删掉了(390e-391a)。诗教中对诗歌形式的讨论涉及“模仿”,这一部分的讨论与第十卷和格劳孔的讨论不一样,那里对格劳孔的教育是哲学教育,这里对阿德曼托斯的教育是道德教育。对阿德曼托斯的诗教不是杜绝模仿,而是说你不能去模仿低于你的人,包括女人,包括工匠。苏格拉底说,只有这样,城邦里鞋匠总是鞋匠,武士总是武士,而不会在武士之外还要去做商人(397e)。这里针对的便是阿德曼托斯先前当小店主和钱商的理想。
三、阿德曼托斯的三次发难
从第四卷开始,阿德曼托斯对苏格拉底一共有三次发难。第一次发难在第四卷开头419a。这时,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已经联手建立了一个兵营式的城邦。阿德曼托斯质疑说:这些雇佣兵式的护卫者幸福吗?我相信,阿德曼托斯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之前“健康城邦”里的雇工,那里雇工服务的是其他职业,而这些雇佣兵式的护卫者服务的是城邦的其他人。健康城邦里的阿德曼托斯不愿做雇工,这里阿德曼托斯不愿做雇佣兵式的护卫者,因为这都是辛苦还挣不到多少钱的职业。苏格拉底接下来对他的长篇大论的“教育”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熟悉的,那就是,护卫者要追求的是城邦的整体的幸福,而不是自己的幸福。最后阿德曼托斯也接受了这一“教育”,就像我们一样。阿德曼托斯接受这个教育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再关心护卫者有没有钱,而去关心城邦有没有钱,关心城邦不要贫富分化,关心城邦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如何应对战争。苏格拉底给他的解决方案是说:你这个城邦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搞外交嘛,你可以合纵连横,告诉另外一个城邦,反正打我们也搞不到钱,正好我们可以合起来打第三个城邦,钱归你们。阿德曼托斯从此获得了一种外交的或者说政治的智慧。但是阿德曼托斯对钱的隐秘的爱好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不再关心自己的钱袋,而是关心城邦的钱袋,那些市场、港口的税收等等经济立法的问题事实上也留给他了。
阿德曼托斯的第二次发难是在第五卷开头。本来,婚姻生育应该本着“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的原则,苏格拉底在之前就提到过了(423e-424a),那个时候阿德曼托斯没有疑问。但恰恰是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进行了关于灵魂三分的对话后,玻勒马霍斯和阿德曼托斯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是关于灵魂三分的对话中关于欲望部分的讨论,使得玻勒马霍斯和阿德曼托斯重新去思考这个原则。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关于欲望的讨论中,格劳孔主要关心的是血气和欲望的区分问题,但对旁听的阿德曼托斯和玻勒马霍斯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每一种欲望都有它们各自的对象,而不能用对金钱的欲望涵括。在第四卷开头阿德曼托斯抱怨武士没有钱的时候,苏格拉底其实就提醒过他,苏格拉底说没钱除了你说的那些不便之外,还包括没法给女友(lady companions)买礼物,言下之意是没钱你的爱欲怎么实现呢?(420a)但那时阿德曼托斯忽略了这个问题,他太爱钱了,以为所有的欲望都能被爱钱的欲望涵括。但在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完成了有关灵魂三分的讨论之后,阿德曼托斯重新提出了妇女儿童的共有问题,妇女儿童的共有涉及到爱欲,爱欲与金钱欲中分开了。
《理想国》里最好玩的部分就是第五卷描绘的这个妇女儿童共有的城邦。这当然是一出喜剧。第一波,女人也可以当武士;当武士之后,女人要和男武士一样裸体锻炼。苏格拉底描述了这个场景:“不仅年轻女子这样做,还有年纪大的女人,也像健身房里的老头儿一样,皱纹满面的……坚持锻炼。”(452b)按照习俗的观点,这是一个可笑的场景。但苏格拉底马上就说,习俗上可笑的事情在自然上不一定可笑。不过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把可笑的事情展示给你,让你笑;但如果有人把一个可笑的事情变得不可笑了,那这本身就是可笑的,这也是一种喜剧的手法。在苏格拉底描述这个可笑的场景之前,格劳孔就笑过了(451b)。在整个《理想国》里,格劳孔笑了两次(398c,451b),阿德曼托斯一次都没笑。这不奇怪。阿德曼托斯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可能并不适合笑的教育。苏格拉底曾经尝试过——他在阿德曼托斯提到悲剧属于模仿时(394b),就曾提醒过他喜剧也属于模仿。在第三卷,苏格拉底对他进行了哭的教育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笑的教育。那里,哭的教育目标在于勇敢,而笑的教育目标似乎在于节制(388e-389a)。可是,对于阿德曼托斯这个缺乏勇敢的人来说,难道不应该把笑的教育也归于勇敢教育吗?对那些真正可笑的事情要敢于笑。悲剧是由模仿高于你的东西产生的,比如神,而喜剧是由模仿低于你的东西产生的,比如动物。妇女儿童共有就是在模仿公鸡、猎狗和马(459a-b)。可惜,对阿德曼托斯的这个教育失败了。
妇女儿童的共有只有在哲学家做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以后才能实现。针对哲学家,阿德曼托斯提出了他的第三次发难。他质疑说,在实际中我们看到的学哲学的人大部分变成了怪人,即使不说是坏蛋,最好的也不过成为对城邦无用的废物。仔细看,其实苏格拉底同意阿德曼托斯的大部分判断。在496b-c,苏格拉底讲了几种适合学哲学的例外情况:(1)出身高贵,也受过良好教育,但因为处于流放之中从而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从事哲学;(2)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的城邦,又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城邦的事务;这两种情况都和阿德曼托斯没关系,他生在雅典,也没有处于流放之中;(3)少数天赋优秀的人,脱离了他所正当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了哲学;这也不可能是阿德曼托斯,因为他并未藐视其他技艺;(4)类似Theages的情况,病弱的身体使他脱离了政治,没能背离哲学,阿德曼托斯身体也弱,但显而易见,身体弱并不是成为哲学家的充分或必要条件;(5)苏格拉底本人这种自带神示的情况,这更是和阿德曼托斯没关系。其实前四种情况都是“被迫”从事哲学的情形,真正的哲学家只有苏格拉底一人。如果说阿德曼托斯也是个政经哲PPE的学生,经过《理想国》中的教育,他终于从E(Economics)到达了第二个P(Politics),即从小店主变成了城邦的护卫者,仅此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理想国》的目的是让所有参加者都去学哲学,就像政经哲的教育,并不是建立一个从哲学到政治学到经济学的鄙视链。我们看看参与这场对话的其他人,比如格劳孔,他也出现在《会饮》的框架对话中。Apollodorus说格劳孔的现状是:“干什么也比搞哲学强!”(《会饮》173a)玻勒马霍斯有点奇怪,《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提到他的时候,让他转向哲学(《斐德若》257b)。还有克勒托丰。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他是色拉叙马霍斯的学生之一。在《克勒托丰》这部对话里,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跟着色拉叙马霍斯,而不是苏格拉底:“对于那些还没有转向追求德性的人,你苏格拉底很有价值;对于那些已经转向追求德性的人,你却挡住了他们通过达致德性目标而获得幸福的道。”(《克勒托丰》410d)。或许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理想国》491b这段话:阻碍人们从事哲学的恰恰是勇敢、节制这些人所称赞的德性,阿德曼托斯对此感到荒唐,不能理解。或许搞哲学需要一种《斐德若》中讲的那种迷狂,而阿德曼托斯缺乏的就是这种迷狂。
四、阿德曼托斯的退场
阿德曼托斯在柏拉图对话中的退场是在《巴门尼德》的框架对话中。《巴门尼德》主体对话戏剧时间是前450年,那时苏格拉底刚刚19岁成年;框架对话的戏剧时间是公元前382年,也就是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十七年后。框架对话的情节是,一个叫做克法洛斯的外邦人到达雅典,在市场上遇到了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兄弟。阿德曼托斯对克法洛斯说道:“欢迎你,克法洛斯,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你的话,请告诉我们。”这个外邦人也叫克法洛斯,自然让我们想起《理想国》中那个老克法洛斯,想必他现在早已过世;市场,自然也是《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留给阿德曼托斯的位置。那么这个新的,爱智的克法洛斯想让阿德曼托斯他们帮什么忙呢?他想要找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的兄弟安提丰,因为安提丰曾经从Pythodorus那里听到过苏格拉底在年轻时与巴门尼德、芝诺的一次对话,他们现在想从安提丰那里完整地再听一次。然后阿德曼托斯说,安提丰年轻的时候的确把这次对话搞得滚瓜烂熟,但现在他却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马术上。当他们到安提丰家的时候,安提丰的确在让铜匠整什么马具。直到把铜匠打发走,安提丰才开始转述这场苏格拉底刚成年时曾经参与过的对话。“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没有从事哲学的阿德曼托斯,把新一代爱智者引向了那个被一代代转述的哲学家在19岁那年的第一次登场,这就是阿德曼托斯的退场。